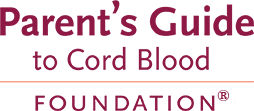当前位置
Shai的故事

Shai Miranda Verter
1992年12月9日 - 1997年9月2日
Shai的故事从我开始,我是她的母亲(Frances Verter)。在Shai出生前,我拥有一份成功的事业,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从事天文学研究。1992年,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决定成为一名单亲母亲,并为我的女儿取名Shai,以纪念我的父亲。
Shai出生时骨盆内就存在恶性肿瘤(称为横纹肌肉瘤),但这块肿瘤直到她八个月大时才发展到引起注意,而且在她十一个月时才得以确诊。在那时,肿瘤已转移到她的肺部。于是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癌症治疗,期间辗转于三家不同的医院。Shai每三周就需要接受化疗,随之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感染和输血。在一场持续十二个小时的手术中,Shai的残留肿瘤被切除,同时被切除的还有三个内脏器官。随后,她经历了长达数周的放疗,包括短距离放射治疗(放射性植入物 )。
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之中,Shai始终保持着非凡的勇气。癌症患儿的耐受能力都令人敬畏。孩子们天生就知道享受当下,无论他们昨天曾经经历什么或者明天可能面临怎样的痛苦。作为成年人,我们一辈子都在想重新获得孩提时代在压力下生活的能力。我还发现,无论在医院以外有着怎样的生活轨迹,有患病孩子的家庭全都有着相同的感受。
下面的这件小事真切地体现了Shai的性格: 有一天,我拿着我们的衣服下楼去医院的洗衣房,让一位前来探访的十多岁的小客人陪着她。(我总是在汽车后备箱里放着一个行李箱,以防Shai住院。有时我们会靠那个箱子生活好几周。) 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一名住院医生走进来,想要给Shai做检查。她坚决地告诉他,没有母亲在场,任何人都不能给她做检查。医生试图用一把形似小鱼的小手电筒逗她开心。他们玩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说服了医生把这东西送给她。之后她便有礼貌地请大夫离开了。等到我回来时,大夫刚走,只看到小客人被Shai的机智逗得笑得不停。除了很有主见外,Shai的脾气也很犟,从来不喊疼。只看外表的话,你绝对猜不出这姑娘这么坚强。
在Shai接受治疗期间,我们得到了多种形式的慈善捐助。例如,在1994年,我总共有5个月时间在医院陪护Shai。多亏了我科研机构"大学航天研究协会"(Universities Space Research Association)同事们捐赠的休假,我才得以保住工作,还能享受医疗保险。另外,我在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同事们也协调组织了接连不断的献血活动,Shai的所有输血基本都来自这些直接的捐助。
在结束肿瘤化疗后,Shai进入完全恢复期,她的故事似乎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她开始和同龄的孩子一样进入学前班,我也努力准备把之前手头的研究工作赶紧拿起来。我遇到了另一位单亲父亲,并且很快就订婚了。我们在1996年的万圣节结了婚。没想到六天后,Shai就被诊断患“继发性”白血病,一种因既往的抗癌治疗诱发的白血病。
Shai此时需要干细胞移植。脐带血移植当时尚未普及,于是我们努力寻找匹配的骨髓捐献者。Shai的父亲和我种族背景不同,而且偏偏不巧的是,Shai遗传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类型(HLA型)。经过数月的跨国搜寻,我们最终找到了一名匹配的骨髓捐献者。在绝大部分时间里,Shai和我都生活在一家儿科医院的隔离病房里。
Shai的骨髓移植存在相当高的风险,因为高强度的化疗和放射已经透支了她的身体。在移植大约十天后,她出现了肝功能衰竭(注:此前她曾经遭遇过两次,但都得以生还)。癌症治疗团队把全家人叫到一个小会议室里,下了病危通知书。有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对Shai使用大剂量的血液稀释剂来消除肝脏凝血,但是她也许会因大出血死去。而如果不这样做,她肯定会因肝功能衰竭而死去。我们决定放手一搏试一试血液稀释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Shai注射了有史以来比任何孩子都多的“TPA”血液稀释剂。她开始康复。但随后她又出现了心脏衰竭(心肌症 )。
Shai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她的情况非常不稳定,全家人接到病危通知,称她很可能在一小时内去世。但最终她没有离去。没有人想到她能挺过那一夜,可是她做到了。全家人被告知,移植后如果出现多器官衰竭,致死率是100%;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坚持的意义不大,还不如直接拔掉生命维持设备。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只要Shai还没有放弃,我们就继续坚持。Shai逐渐康复。她离开了重症监护室,随后出院,入住了一处“麦当劳叔叔之家”(Ronald McDonald House)。医生和护士们给她取了个昵称叫“34号街的奇迹”,因为费城儿童医院(CHOP)就在34号街上。提出拔掉生命维持设备的大夫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并且表示: “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Shai的故事似乎再一次有了迎来圆满结局的希望。然而她的白血病又一次复发,她回到了家,在临终关怀中去世,陪伴左右的是她的家人和宠物。我伤心欲绝,如果老天注定要带走Shai,为什么还让她在重症监护室那么久备受折磨?
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由此开始。我很快再次怀孕,在40岁的年纪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在42岁时生下了第三个女儿。我放弃了天文学研究领域的工作,因为一方面这份事业因为我在医院里度过的时光而被完全荒废,另一方面我希望有更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我在NASA的一家合约商那里找到了一份辅助工作,给一个研究气候模型的团队写程序。
在第二次怀孕时,我决定自体储存脐带血。我深切地感受到寻找匹配的移植捐献者是有多么艰难,而且我知道最好的配型就来自于家人。我并不希望另一个孩子患上癌症,但我希望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健康保障。我努力研究了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出现的私人脐带血库,整理成了“给家长的脐带血手册”(Parent's Guide to Cord Blood)网站。慢慢我囊括了覆盖全球的自体脐血库,后来又添加了接受捐献的公共库。剩下的就水到渠成了。这个网站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需要投入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2007年,我建立了一个董事会,并根据美国第501(c)(3)条法规建立了基金会。
可以说,Shai的故事是我自己的延续,她的许多经历都来自于她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母亲,下定决心寻找最好的治疗方案,不远万里也要前去寻找。Shai的精神教会了我很多仅靠自己是绝对不可能了解的事情,并让我的人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如今这已成为我的使命,倡导父母保存脐带血和获得脐带血治疗。有时,帮助这些父母需要经受来自特殊利益群体的压力。在某些无形的层面,由一个经历过癌症丧女的母亲来主导正是这个基金会最大的力量来源。